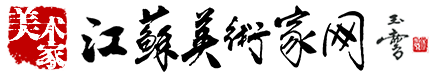历史记忆的现代观照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油画作品观后感
| 2017-08-18来源:中国美协 |
徐 虹
中国的美术家和历史学家历经五年,完成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巨大任务。这是继2009年由中国文联和文化部发起,国家财政支持的“重大历史题材画创作工程”之后的又一重要项目,完成国、油、版、雕作品约一百五十余件,其中油画50件,占总量三分之一。 这次“美术创作工程”的内容是“主要表现自公元前有中华人文活动记载以来至1840年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即中国史前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史实、涌现的杰出人物和文明成果”。也就是说,此前完成的“重大历史题材画”,是1840之后发生的中国社会演变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而1840年之前上下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则是这次“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内容。 中国古代描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图像很少存遗存,民间流传很少,或只能在石窟和墓室壁画上看到零星片段。而在历史文献中有关图像的记载也不多,因而“左图右史”的盛概只能出现在今人的想象之中。清代有描绘帝王政治军事活动的图绘,但规模较小形不成系列,更不要说追述描绘历朝历代的历史事迹了。当然这不能归咎于材料限制——比如帛、泥、纸的难以保存等,因为中国有石雕,西方也有壁画和纸本,结果是我们没有具有规模的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留存。这既和中国文化习惯于用文字描述历史有关,也和历代统治者严密控制思想有关,更与改朝换代,战祸频仍,毁灭文物有关!
谈到历史,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包括事物、事态、事情的转换,开始和结束的过程。在事件过程中的遗存,如绘画、传记、传说、歌谣等。以及由于历史的记载和遗存带给人们的感受,它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在人们生活中发挥或明或暗的作用,在意识深处影响着后来人们的感情选择和价值判断,影响人们的当下生活和对未来的期待。这就是记忆中的历史对人们的影响,包括人们言说历史的立场、态度和看待历史的视角。所以,艺术家创作历史画不仅仅是要描绘某一时空中的某一静止的点,更是要描述“一段”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活的有丰富内涵的历史。雅各布·布格哈德撰写的《希腊人与希腊文明》中对希腊文化本质的的提炼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这是通过对希腊的赛会精神,悲观主义,城邦政体等各种事物的考察和具体描述来显现的。而作为一名文化史家和艺术史家,更是发挥了对希腊的艺术、宗教、经济生活等诸多方面的独到见解,给我们展现了希腊文化丰富而又变化细微的全貌,读来充满细节和富有情感,被誉为现代关于希腊文化的第一次,也是最好的解释。所以,虽然艺术家用形象描绘历史与历史学家用文字叙事不同,但在本质上,在关于合乎逻辑和有洞察力上是相通的,艺术家通过赋形历史事件中人物和环境,来绘就我们“认可的”历史图景。 由于近百年历史事件与人物离我们比较接近,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以及生活氛围与近百年的过程紧密相连。一些历史问题还在继续反思之中,一些历史进程还在延续,过去不久的故事还存贮在记忆里,亲历者的经验还历历在目……总之, “近百年”离我们很近很近,近到我们甚至分不清究竟是不是已经逝去,它仍然给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张,因为当我们指认这些“历史”时,实际是对“现实”作判断。而在艺术领域,这些“历史题材”曾经有过“经典样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两次组织艺术家创作“革命历史画”,那些历史画作品创作过程的特殊性,作品产生以后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以后创作同类题材的限囿。比如,英雄主义意识,战争和人民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等等,如何在结构、色彩、造型、秩序等形式要素上体现这些关系,都给以后的美术发展留下深刻而具体的印记,它也必然要影响近百年历史画题材的创作课题。 相比较而言,这次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由于“上下五千年”的时空跨度极大,很多历史阶段强调的是“文明史”,是中华民族发现、建构、创造、贡献的历史,区别于近百年来的战争、灾难、牺牲、抗争主题。这对艺术创作来讲显然可以有更为宽广的想象天地,更为自由和流畅的表达空间。但究竟截取哪些图像成为“现场”事件? 叙事结构如何设定?表现形式的可能性等。这不仅是对艺术家历史意识的考察,也是对艺术家的历史态度的考察。它关乎艺术品的历史意义,也关乎“真实性”所在。所以,历史形象的创作也就和讲故事一样,虽然隔代相传时空转换,但还是要让听众津津有味,信以为真。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描绘先秦的几幅油画,如《尧舜禅让》(李建国)、《文王兴周》(陈益明、郭建濂)、《周易占筮》(高小华、雷著华)《仰韶彩陶文化》(郭北平、李望平、张峰)等,这些题材似乎与我们对历史的想象相去不远。依靠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在我们脑海里大体能建构起相应的历史场景,营造一种特定的历史氛围。而艺术家的表现能符合这种氛围,配合考古挖掘出土的器皿服饰道具的形制,作为历史图景的基本功能可让观者得到满足。但是艺术从来不仅仅满足于“图说”的功能,历史画之所以为艺术,就在于艺术的丰富和复杂性,在于人在其中的“发现”和“被照亮”。这几件作品中重要历史人物如尧、舜、周文王,作为中国文明史上神话般的人物,具有象征性。但在处理这些历史人物时没有具体形象可以依从,所以无法像处理近代人物那样可以按照“真实”的相貌去加工;同时,对于这样一种符号化了的文化现象,实际上很难具体化。所以,在这几件作品中我们看到艺术家自觉淡化了“英雄叙事”的习惯,没有了战争和建设所需要的强壮威武的体魄、坚毅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姿势……最终画家显然是将现实生活中我们所感知到的,有道德的人的容颜和神情,气度和修养,身姿和动作表现在画面形象中,将一种可能的现实存在显示于画布,让观众感受到什么是穆穆天子,什么是朗朗君子,何为先民等形象。这也说明要表现千年文化视觉现象,基本靠画家在现实中积累,并以艺术手段的提炼才能够成功。 由此看到艺术家描绘想象中的“历史”,实际是根据自己的修养对“历史”进行“提炼”和“评价”,这是一种和历史对话的机制。既然有对话就必然有“话语”痕迹,这痕迹就是艺术家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的发展过程。在这批创作中,很有意思的是绝大部分作品经过一改再改,不断提升的过程。这里有历史学家提出的细节问题,比如根据历史记载,人物的形象、身材、气质;不同历史阶段的器物和环境特征及社会行为礼仪规范等等,要求作品真实于历史细节。比如许江、邬大勇、孙景刚所作《文天祥》一画,作者最初将历史人物画成一介文弱白衣书生,与彪悍的蒙古人形成对比,但是专家指出文天祥体格魁梧,原有画面不符合历史图景。作为一名壮志满怀,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的历史人物,如何表现他在危难关头的形象,是对艺术家的艺术思想和情感经验的挑战。所以,画家们又将文天祥处理成带着枷锁站立在荒草满坡的原野上的形象。枷锁可能更符合那个时代刑罚的形制,但是当代人难以接受一位民族英雄人物带着它被迫俯就的形象。因为想出这种刑拘的工具就是要迫使“犯人”低首就范,要让对方处于被剥夺尊严的“非人”状态。虽然我们也在其他一些作品中看到带枷锁的历史人物,但那种近距离聚焦表现人物的脸和手的表情以反映内心精神活动,是可能成功的。所以,无论如何,让枷锁卡着人物脖颈,站立在宽广的草原,不知会让观者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预期?当观众在情感上感到别扭,然后被告知这就是当时真实的情况,是否正当?何况这是艺术的创作而不是历史遗留的摄影。最后完成的画面改为主人公带着长长的铁镣铐,显然这能让现代人接受,从视觉上也更完整。当主人公双腕悬挂因沉重而下垂的铁镣,身上的红色衣衫如血样夕阳一般照亮画面时,人物内心的情感力量可以从他脸上的复杂表情,坚强又富有细微变化的身体姿态传导给观众,而前景、中景如燃烧的草原和天空,远处阴沉的天际……这一切又给作品带来更为丰富的意蕴,观众可以通过与这件作品的对话来获得特定历史阶段的印象,溯源事件的起始演变,关注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 作品《楚汉相争》(王宏剑)、《孟子论政》(骆根新、罗田喜)、《范仲淹岳阳楼记》(徐里、李晓伟、李豫闽)、《岳飞》(何红舟、黄发祥、尹华)、《隆庆开海》(麻显钢)、《明代书画艺术》(封治国)、《永乐迁都北京》(王君端)、《唐律疏议与官衙断案》(丁一林)等,都有一种符合现代观众感情期待的倾向。如《楚汉相争》中,画家将“鸿门宴”中关键人物的性格作适度的夸张,如刘邦故作卑微的姿态,项庄舞剑矫健峻拔的身姿,卫士拔剑时的紧张瞬间……周围人的各色表情和动作,加上夜间室内的光线处理,戏剧性地渲染了这一决定刘、项命运的历史节点。这类具有戏剧性的题材,使历史画有引人入胜的观赏性,画家的构思处理填补了史实的空缺,构成情境交融的历史现场。 50年代罗工柳的油画《地道战》,已成为那一时期人们对抗战中地道战想象与记忆的历史场景。今天的画家在处理这类“历史情境剧”时,无论在造型能力还是在气氛营造,无论是故事的演绎技巧还是画面整体的控制,或者具体细节的描绘与人物个性的刻画乃至光线和色彩的处理,都已“今非昔比”。但在表现能力明显增强的同时,如何取得一种历史叙事的经典性和“合法性”,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几千年历史相传的原因,人们情感中的历史“记忆”更为复杂和个性化,画家表现历史人物要达到深刻而真实,不能简单化和漫画化,这是对画家“基本功”是否过硬的又一考验。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因为要表现的是民族记忆“深处”的历史,而使“艺术地”讲述历史成为可能,这与近现代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太近,材料繁多细节丰富,取舍难度大,而意识形态规定性高,个人发挥空间有限的创作环境有很大的不同。正由于这样,虽然“五千年文明史”年深日久,资料稀缺,但画家反而可以有较为自由的想象空间,可以以自己的艺术手法来填补缺失的“历史”。如《夏都二里头》(黄启明、顾亦鸣、罗海英)、《战国争雄》(章德明)、《石窟艺术》(张俊明)、《宋慈洗冤集录》(王耀伟、孙志纯、丁铮)、《土尓扈特回归祖国》(吴云华、高阳)等作品的成功都与此有关。夏都二里头的历史考古本身云雾重重,因为历史久远,重要证据尚付阙如,画家将夏朝都城用一种抽象的几何风格画出,这种本身不确定性的表述,反而让画面具有一种象征意味,就像漂浮几千年时空之中的迷蒙云气,在显示其神秘气质之时也引导人们浮想联翩……《战国争雄》画家有意用充满表现性的笔触表现剧烈动荡的时代气氛,在近看似乎只有飞动的笔触,色彩和色形的胶着,对比,互相渗入,眼花缭乱之际退远一步,才发现是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壮阔战争场面,使人由衷佩服艺术家目标清晰以及和目标一致的形式手段。 《石窟艺术》的胜出在于气势,以极低的视平线强调夸张了石窟塑像的伟岸雄壮,抬头仰望的开阔意象,意味艺术和宗教给人带来的精神提升。《宋慈洗怨集录》的艺术特殊趣味在于光的处理,平光和逆光带来画面明亮闪烁的视觉效果,这种光线下的形体塑造可以有线性的特别流畅的意味,同时也可以将形体描绘得很坚实,这是在西方现代艺术中常用的描绘人物手段。这种散漫的光线较固定光源的描绘,具有更多自由安排画面的人物、表达细节、凸显强烈感情色彩的优势。而《土尔扈特回归祖国》一画让人回想苏里科夫一些大型油画的结构和处理手段。大笔触,略带俯视的构图,给这大画幅带来全景般的宏大气势。远处朝霞照亮了雪山,那鲜艳的光色对比翻越山峰而来的大队土尔扈特人的冷色调显出一种戏剧般的强烈效果。那些身穿翻卷皮毛厚衣的人们,挎着刀,扛着枪,刚翻越雪山行进在积雪的坡地,其间夹着大队的男女老幼,壮实的牛车上有抱着小羊的孩童和他的家人,还有正拉着马头琴的乐人。他们疲惫但又不乏坚毅的神色,强壮的体格和艰难的处境,严寒的雪山风口与他们坦荡的神态,这种艰辛与勇气交集的情景,在视觉上给观者心理造成震撼。这件作品突出了油画表现的优势,冷暖色对比,空间透视的运用,材质肌理对比,绘画性的用笔,这一切使画面自然有节奏变化,厚重浓郁而有丰满感。 总之,这次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给中国历史画序列添加了有历史分量和艺术分量的作品。总体来讲,这些作品在努力通过可视的历史氛围带观众进入历史情境,这种氛围不仅仅由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衣着配饰,日常用具,地域环境等组成,也由那个时间段发生的事件中有关的人物,人物的性格,他(她)的气质,以及现代人观看他们的视角所组成。我们通过艺术家对史料的“表现”看到历史的“真相”,也看到了当代艺术家对历史的认识和他渗入史实的情感立场。这就是“历史画”存在的理由。所以,今天的艺术家对历史画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今天人们对历史的想象和认识。再过一百年,人们看这些历史画,就会从中吸取今天人们的历史知识,包括对历史的认识。这种认识来源不只是局限于文献记载,因为那些历史文本实际上是选择后的留存,是添加和删去的遗迹。所以,今人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加和删去,一百年后的人们也会这样做。 我为前次“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写的文章《对话:历史与历史性绘画中》中提到:“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因为人是历史中的人。‘重大历史题材画’是参与创造历史‘图式’的方式。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实际上是在向公众回答如何叙述历史,叙述目的为何等问题”这既是讨论中国历史画的基础,也是中国历史画必须面对的课题。“没有艺术家对历史“形象的显现”(电影、戏剧、电视剧等也是艺术的显现),历史往往是人们头脑中的一些概念,或是书本记载的文献。人类对待在时间流中展示的人类行为和事件,是可以有不同的想象和解释的。但追求“真实”是符合人类追求真理必然性本质的。“历史性绘画”从艺术的途径,满足了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这也就是弥补了历史画空缺的“中华文明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王洁 |
- 上一篇:没有了
- 下一篇:历史的审美叙事与图像建构 ——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论纲
- 上一篇:没有了
- 热点内容